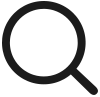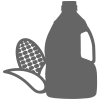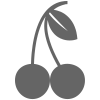永州市
远去的吆喝声
作者:李一凡
入夜,旧时零陵街头,灯光昏暗,行人稀少,大街上也只有几家店铺在营业,商家不到二更天(晚上九时)就打烊关张。这时若要寻吃的,街上流动的小吃担贩却正是热闹的时候,只听那“米豆腐啰”“馄饨面啰”“饺饵噢”“甜酒冲鸡蛋唻”的吆喝声不断;深夜还可以看见小贩们挑着热炭炉和食品,手提着马灯或灯笼,沿街叫卖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蒋军兆先生在零陵县人民政府工作,常常加班到深夜,疲劳了,饥饿了,便到街上叫一个小吃担贩,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馄饨或米豆腐,饿困全无,那真叫爽快!老先生如此回忆那远去的往事。
我童年的时候,晚上已经听不到小吃摊贩的吆喝声,白天仍然可以看到街上一些收荒货(废品),卖叮叮糖、油炸粑粑的小商贩。印象很深的是“叮叮糖”,摊贩用一个小铁棒敲打着一块小钢片,“叮叮”作响,并吆喝着“吃叮叮糖唻”,引得小学生们围在摊担旁,争先恐后地买糖吃。小贩用一块刨刀形的钢片,经敲打,楔入簸箕般大的麦芽糖饼内,将糖饼切成小块出售。这种敲打钢板的“叮叮”声音,也就成为糖的名字。我很嘴馋,身上若积攒了五分钱,定会在路上买一块“叮叮糖”,享受那唇齿遗香甜的乐趣——难以抹去的童年滋味。
过去做小生意的摊贩喜欢大声吆喝,以招揽客人。我小时候常常到解放路的人民剧院门口玩,那里的小广场很热闹。卖小吃的、卖草药的小摊贩不少,还有杂耍的,吆喝声此起彼伏,生怕路人听不见。我最感兴趣的还是“西洋镜”摊子,那老板真有点功夫,一边敲锣打鼓,一边唱戏,还大声吆喝着:“快来看西洋镜呀!里面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孙猴子、白骨精都有啊,好看得很噢!”孩子们围了一大圈,一毛钱看一场。我好不容易从家里要了一角钱,终于看了一场“西洋镜”,伏在戏匣子的玻璃孔上,一幅幅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的美景图迎面而来,还有锣鼓伴奏,很是开眼,真叫过瘾!
旧时街头的摊贩,除了卖货的,还有剃头的。那时的剃头师傅常常挑着一副剃头担子走街串巷,吆喝着“剃头啰”。我外公姓张,也是一位剃头师傅,而且还是南门有名的“剃头张师傅”。早年家里很穷,外公十几岁就从乡下到城里讨生活,学的手艺就是剃头。三年学徒出师后,他就挑着一副担子到街头理发,把零陵城里的大街小巷都走遍了。他的手艺很好,若给人刮光头,手挥剃刀,三下五除二,不经意间就刮了个光光溜溜;人们喜欢找他剃头,亲切叫他“剃头张师傅”。后来攒了钱,外公在南门街上购置了一间铺面,由行商变成了坐商,但那一副剃头挑子没有丢弃。他家离零陵县立中学很近,与老师们的关系也好,几乎包揽了学校的剃头生意。下课休息时间,外公就挑着担子去校园内,吆喝着学生们来剃头。他不仅手艺好,服务也好,总能将顾客侍候得舒舒服服。有一个故事:县中有一位学生患有头癣,老是治不好,头发脱落不少,人称“癞痢壳子”。外公听说后,弄来了民间药方,居然治好了这个学生头上的“癞痢”。学生非常感激,逢人就说“张师傅好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某日,外公理发店来了一位带有4名警卫员的军官,将外公唬了一大跳,以为犯了什么事。军官来到店里,脱下军帽,头上的旧疾痕迹仍然,原来这就是当年那位“癫痢壳子”。他后来去了延安,现在已是解放军的一位大首长,专门带了礼物来看望外公。他看到店里那副剃头挑子很亲切,还请外公再为他理了一次发。
外公的剃头活一直干到八十几岁才收手,后来一直住在我家养老,成了我最要好的“伙伴”,听他唠叨过去的事,是难得的快乐。一九六七年的秋天,九十岁的外公溘然而去,无疾而终。失去了这位天天相伴的“伙伴”,我很伤心。一直还记得外公的音容笑貌及他老人家的故事。
改革开放以来,个体经济又活跃起来,街上的摊贩也多了起来。但随着时代的变迁,小商贩卖货的习惯也跟着改变了,过去那种吆喝声很难听到了。我每次回到水晶巷老家,常常会花2元钱,到巷口母女俩摆的油炸粑粑摊,买一串金黄油亮、外焦内嫩、又甜又香的油炸粑粑,重温儿时的味道。但,我也没听到母女吆喝,如今的小贩不再靠吆喝招揽生意,那“吆喝”声似乎成了远去的记忆。
虽然没有了“吆喝”声,但那人间烟火味仍然很浓。